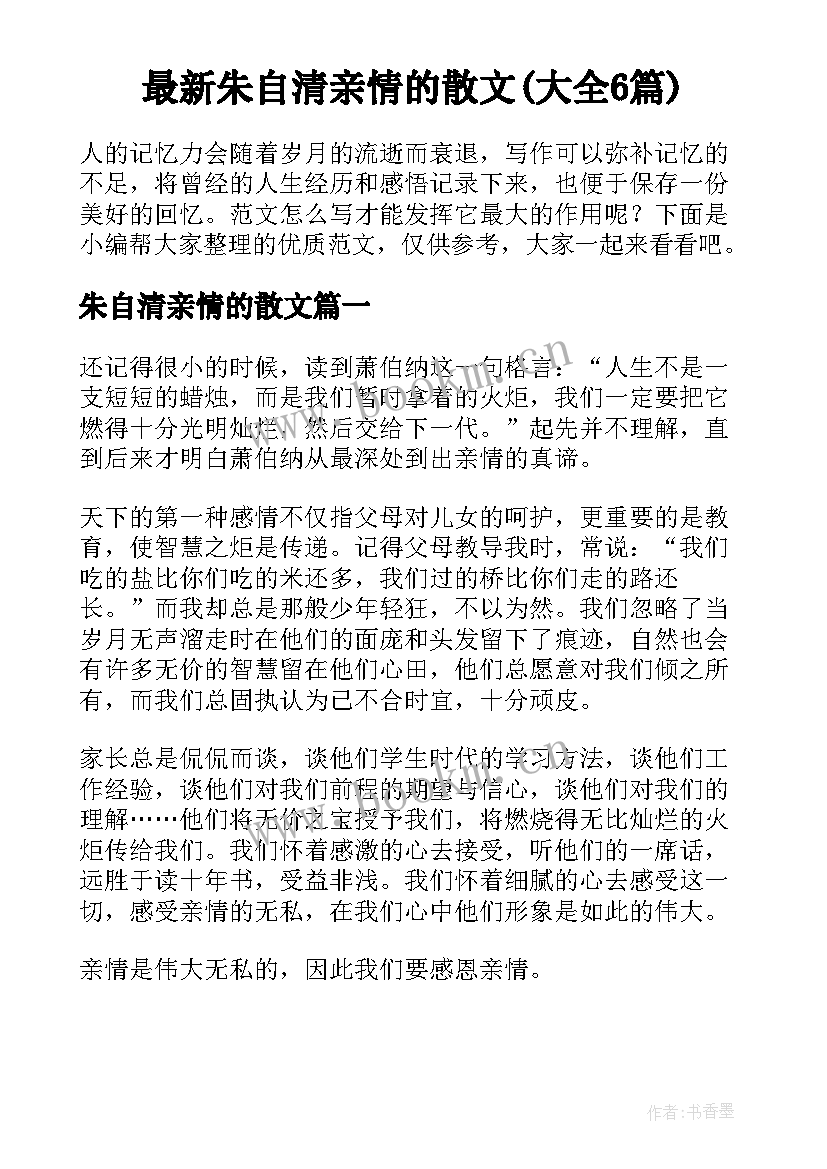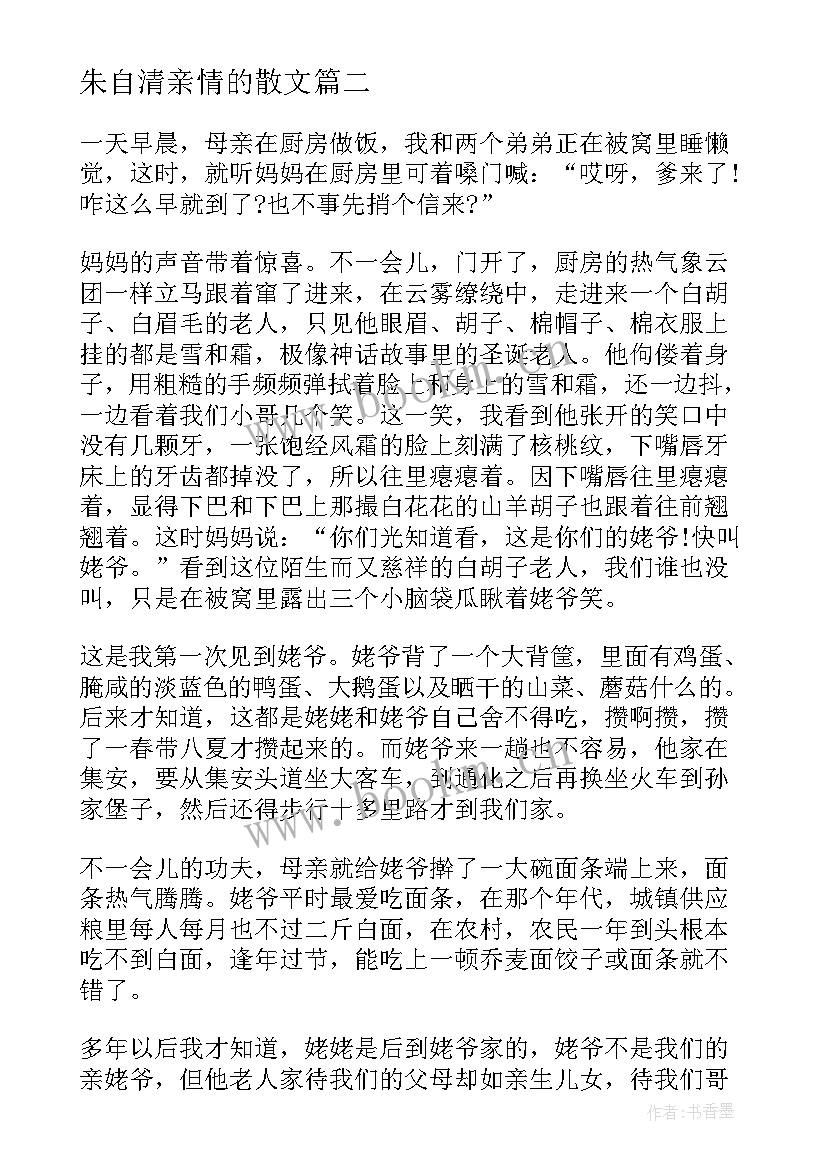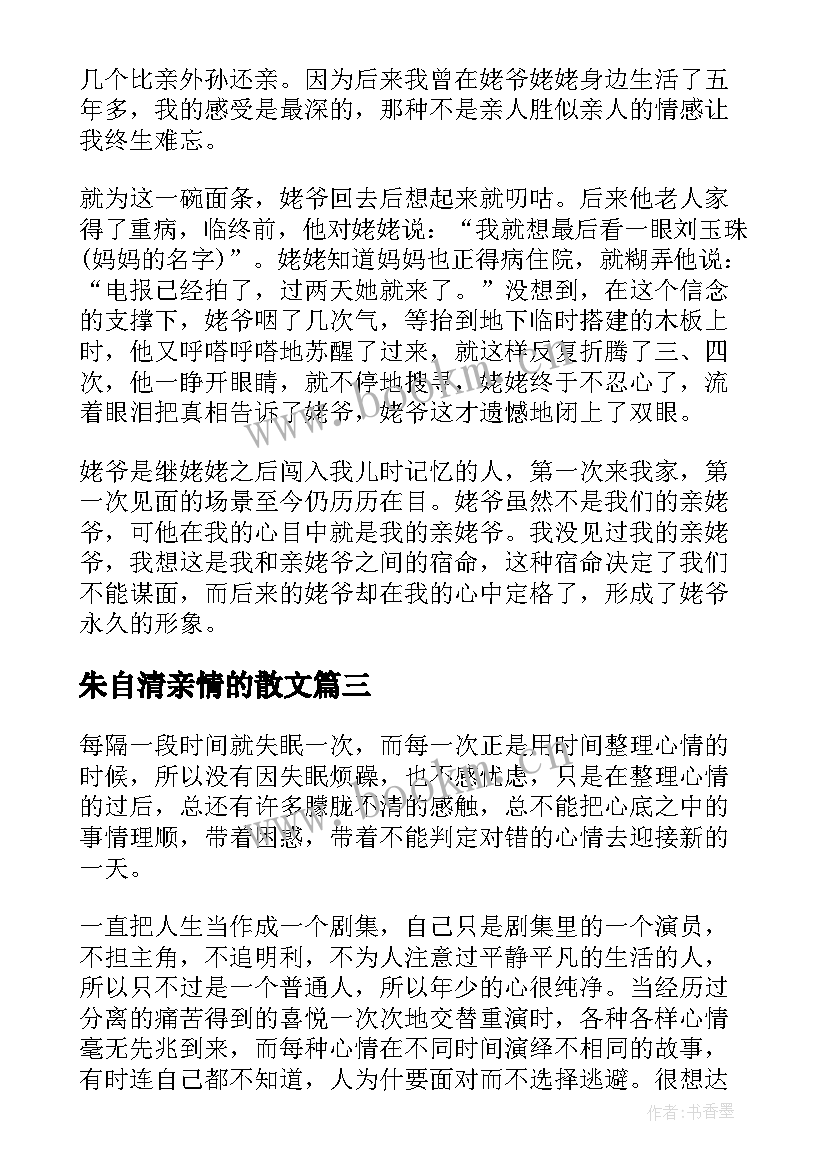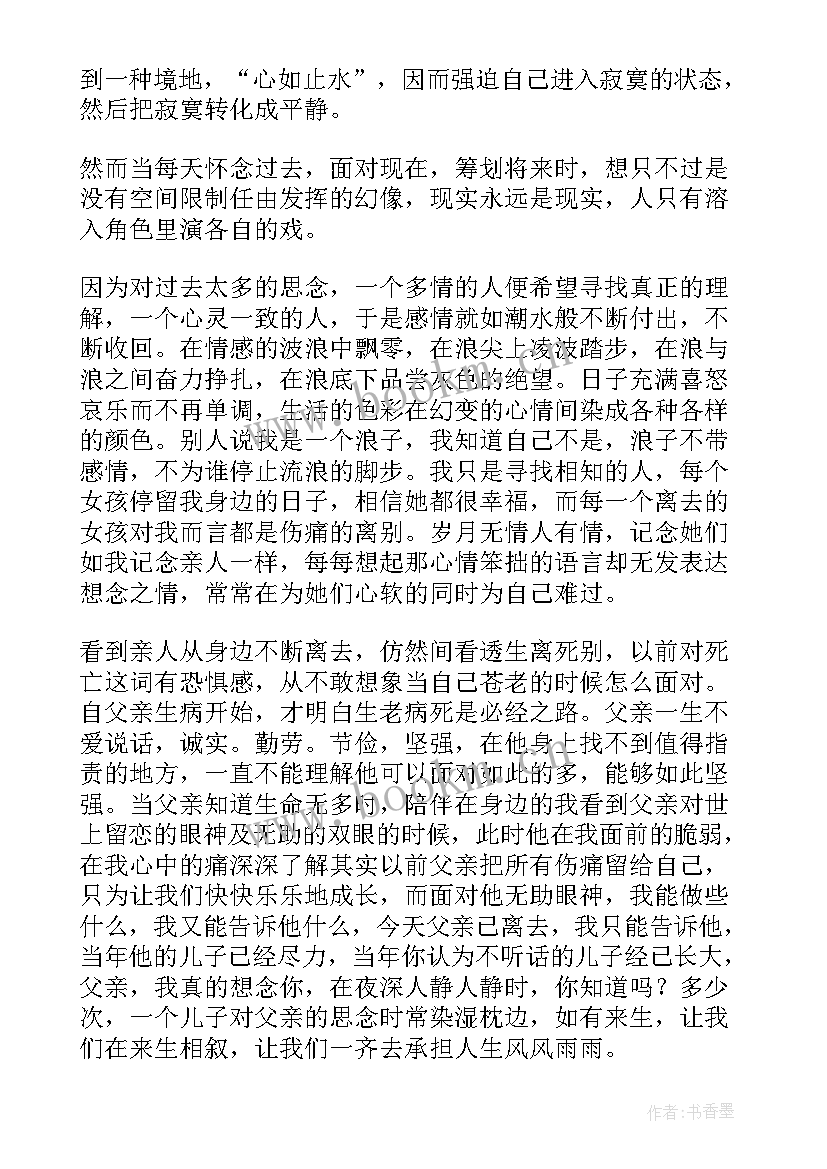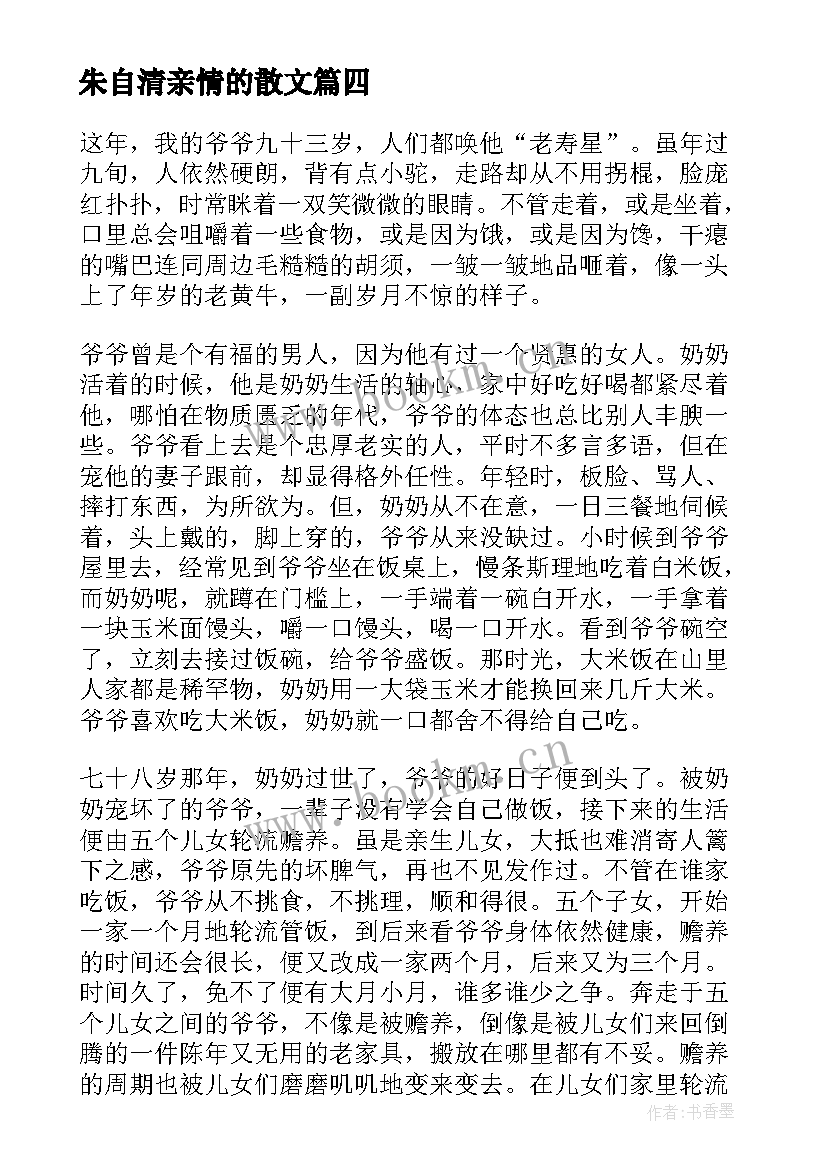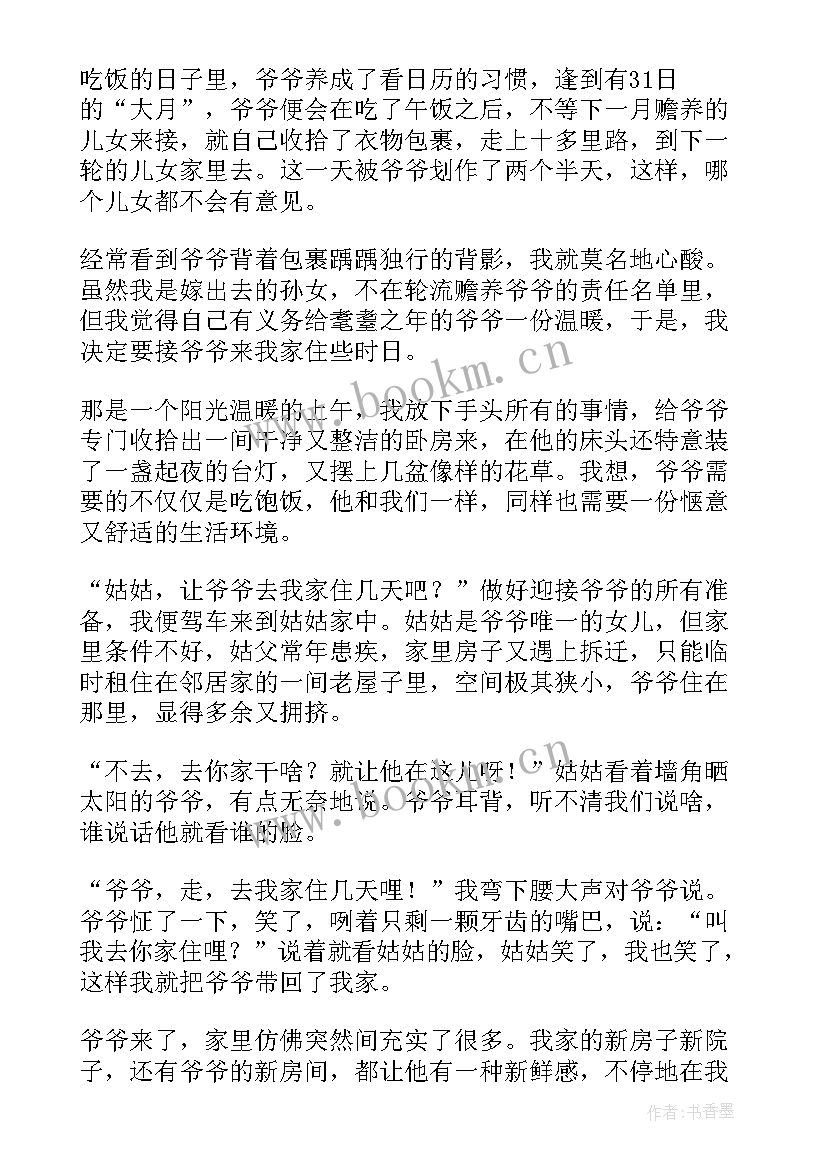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朱自清亲情的散文篇一
还记得很小的时候,读到萧伯纳这一句格言:“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起先并不理解,直到后来才明白萧伯纳从最深处到出亲情的真谛。
天下的第一种感情不仅指父母对儿女的呵护,更重要的是教育,使智慧之炬是传递。记得父母教导我时,常说:“我们吃的盐比你们吃的米还多,我们过的桥比你们走的路还长。”而我却总是那般少年轻狂,不以为然。我们忽略了当岁月无声溜走时在他们的面庞和头发留下了痕迹,自然也会有许多无价的智慧留在他们心田,他们总愿意对我们倾之所有,而我们总固执认为已不合时宜,十分顽皮。
家长总是侃侃而谈,谈他们学生时代的学习方法,谈他们工作经验,谈他们对我们前程的期望与信心,谈他们对我们的理解……他们将无价之宝授予我们,将燃烧得无比灿烂的火炬传给我们。我们怀着感激的心去接受,听他们的一席话,远胜于读十年书,受益非浅。我们怀着细腻的心去感受这一切,感受亲情的无私,在我们心中他们形象是如此的伟大。
亲情是伟大无私的,因此我们要感恩亲情。
朱自清亲情的散文篇二
一天早晨,母亲在厨房做饭,我和两个弟弟正在被窝里睡懒觉,这时,就听妈妈在厨房里可着嗓门喊:“哎呀,爹来了!咋这么早就到了?也不事先捎个信来?”
妈妈的声音带着惊喜。不一会儿,门开了,厨房的热气象云团一样立马跟着窜了进来,在云雾缭绕中,走进来一个白胡子、白眉毛的老人,只见他眼眉、胡子、棉帽子、棉衣服上挂的都是雪和霜,极像神话故事里的圣诞老人。他佝偻着身子,用粗糙的手频频弹拭着脸上和身上的雪和霜,还一边抖,一边看着我们小哥几个笑。这一笑,我看到他张开的笑口中没有几颗牙,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上刻满了核桃纹,下嘴唇牙床上的牙齿都掉没了,所以往里瘪瘪着。因下嘴唇往里瘪瘪着,显得下巴和下巴上那撮白花花的山羊胡子也跟着往前翘翘着。这时妈妈说:“你们光知道看,这是你们的姥爷!快叫姥爷。”看到这位陌生而又慈祥的白胡子老人,我们谁也没叫,只是在被窝里露出三个小脑袋瓜瞅着姥爷笑。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姥爷。姥爷背了一个大背筐,里面有鸡蛋、腌咸的淡蓝色的鸭蛋、大鹅蛋以及晒干的山菜、蘑菇什么的。后来才知道,这都是姥姥和姥爷自己舍不得吃,攒啊攒,攒了一春带八夏才攒起来的。而姥爷来一趟也不容易,他家在集安,要从集安头道坐大客车,到通化之后再换坐火车到孙家堡子,然后还得步行十多里路才到我们家。
不一会儿的功夫,母亲就给姥爷擀了一大碗面条端上来,面条热气腾腾。姥爷平时最爱吃面条,在那个年代,城镇供应粮里每人每月也不过二斤白面,在农村,农民一年到头根本吃不到白面,逢年过节,能吃上一顿乔麦面饺子或面条就不错了。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姥姥是后到姥爷家的,姥爷不是我们的亲姥爷,但他老人家待我们的父母却如亲生儿女,待我们哥几个比亲外孙还亲。因为后来我曾在姥爷姥姥身边生活了五年多,我的感受是最深的,那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情感让我终生难忘。
就为这一碗面条,姥爷回去后想起来就叨咕。后来他老人家得了重病,临终前,他对姥姥说:“我就想最后看一眼刘玉珠(妈妈的名字)”。姥姥知道妈妈也正得病住院,就糊弄他说:“电报已经拍了,过两天她就来了。”没想到,在这个信念的支撑下,姥爷咽了几次气,等抬到地下临时搭建的木板上时,他又呼嗒呼嗒地苏醒了过来,就这样反复折腾了三、四次,他一睁开眼睛,就不停地搜寻,姥姥终于不忍心了,流着眼泪把真相告诉了姥爷,姥爷这才遗憾地闭上了双眼。
姥爷是继姥姥之后闯入我儿时记忆的人,第一次来我家,第一次见面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姥爷虽然不是我们的亲姥爷,可他在我的心目中就是我的亲姥爷。我没见过我的亲姥爷,我想这是我和亲姥爷之间的宿命,这种宿命决定了我们不能谋面,而后来的姥爷却在我的心中定格了,形成了姥爷永久的形象。
朱自清亲情的散文篇三
每隔一段时间就失眠一次,而每一次正是用时间整理心情的时候,所以没有因失眠烦躁,也不感忧虑,只是在整理心情的过后,总还有许多朦胧不清的感触,总不能把心底之中的事情理顺,带着困惑,带着不能判定对错的心情去迎接新的一天。
一直把人生当作成一个剧集,自己只是剧集里的一个演员,不担主角,不追明利,不为人注意过平静平凡的生活的人,所以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年少的心很纯净。当经历过分离的痛苦得到的喜悦一次次地交替重演时,各种各样心情毫无先兆到来,而每种心情在不同时间演绎不相同的故事,有时连自己都不知道,人为什要面对而不选择逃避。很想达到一种境地,“心如止水”,因而强迫自己进入寂寞的状态,然后把寂寞转化成平静。
然而当每天怀念过去,面对现在,筹划将来时,想只不过是没有空间限制任由发挥的幻像,现实永远是现实,人只有溶入角色里演各自的戏。
因为对过去太多的思念,一个多情的人便希望寻找真正的理解,一个心灵一致的人,于是感情就如潮水般不断付出,不断收回。在情感的波浪中飘零,在浪尖上凌波踏步,在浪与浪之间奋力挣扎,在浪底下品尝灰色的绝望。日子充满喜怒哀乐而不再单调,生活的色彩在幻变的心情间染成各种各样的颜色。别人说我是一个浪子,我知道自己不是,浪子不带感情,不为谁停止流浪的脚步。我只是寻找相知的人,每个女孩停留我身边的日子,相信她都很幸福,而每一个离去的女孩对我而言都是伤痛的离别。岁月无情人有情,记念她们如我记念亲人一样,每每想起那心情笨拙的语言却无发表达想念之情,常常在为她们心软的同时为自己难过。
看到亲人从身边不断离去,仿然间看透生离死别,以前对死亡这词有恐惧感,从不敢想象当自己苍老的时候怎么面对。自父亲生病开始,才明白生老病死是必经之路。父亲一生不爱说话,诚实。勤劳。节俭,坚强,在他身上找不到值得指责的地方,一直不能理解他可以面对如此的多,能够如此坚强。当父亲知道生命无多时,陪伴在身边的我看到父亲对世上留恋的眼神及无助的双眼的时候,此时他在我面前的脆弱,在我心中的痛深深了解其实以前父亲把所有伤痛留给自己,只为让我们快快乐乐地成长,而面对他无助眼神,我能做些什么,我又能告诉他什么,今天父亲已离去,我只能告诉他,当年他的儿子已经尽力,当年你认为不听话的儿子经已长大,父亲,我真的想念你,在夜深人静人静时,你知道吗?多少次,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思念时常染湿枕边,如有来生,让我们在来生相叙,让我们一齐去承担人生风风雨雨。
朱自清亲情的散文篇四
这年,我的爷爷九十三岁,人们都唤他“老寿星”。虽年过九旬,人依然硬朗,背有点小驼,走路却从不用拐棍,脸庞红扑扑,时常眯着一双笑微微的眼睛。不管走着,或是坐着,口里总会咀嚼着一些食物,或是因为饿,或是因为馋,干瘪的嘴巴连同周边毛糙糙的胡须,一皱一皱地品咂着,像一头上了年岁的老黄牛,一副岁月不惊的样子。
爷爷曾是个有福的男人,因为他有过一个贤惠的女人。奶奶活着的时候,他是奶奶生活的轴心,家中好吃好喝都紧尽着他,哪怕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爷爷的体态也总比别人丰腴一些。爷爷看上去是个忠厚老实的人,平时不多言多语,但在宠他的妻子跟前,却显得格外任性。年轻时,板脸、骂人、摔打东西,为所欲为。但,奶奶从不在意,一日三餐地伺候着,头上戴的,脚上穿的,爷爷从来没缺过。小时候到爷爷屋里去,经常见到爷爷坐在饭桌上,慢条斯理地吃着白米饭,而奶奶呢,就蹲在门槛上,一手端着一碗白开水,一手拿着一块玉米面馒头,嚼一口馒头,喝一口开水。看到爷爷碗空了,立刻去接过饭碗,给爷爷盛饭。那时光,大米饭在山里人家都是稀罕物,奶奶用一大袋玉米才能换回来几斤大米。爷爷喜欢吃大米饭,奶奶就一口都舍不得给自己吃。
七十八岁那年,奶奶过世了,爷爷的好日子便到头了。被奶奶宠坏了的爷爷,一辈子没有学会自己做饭,接下来的生活便由五个儿女轮流赡养。虽是亲生儿女,大抵也难消寄人篱下之感,爷爷原先的坏脾气,再也不见发作过。不管在谁家吃饭,爷爷从不挑食,不挑理,顺和得很。五个子女,开始一家一个月地轮流管饭,到后来看爷爷身体依然健康,赡养的时间还会很长,便又改成一家两个月,后来又为三个月。时间久了,免不了便有大月小月,谁多谁少之争。奔走于五个儿女之间的爷爷,不像是被赡养,倒像是被儿女们来回倒腾的一件陈年又无用的老家具,搬放在哪里都有不妥。赡养的周期也被儿女们磨磨叽叽地变来变去。在儿女们家里轮流吃饭的日子里,爷爷养成了看日历的习惯,逢到有31日的“大月”,爷爷便会在吃了午饭之后,不等下一月赡养的儿女来接,就自己收拾了衣物包裹,走上十多里路,到下一轮的儿女家里去。这一天被爷爷划作了两个半天,这样,哪个儿女都不会有意见。
经常看到爷爷背着包裹踽踽独行的背影,我就莫名地心酸。虽然我是嫁出去的孙女,不在轮流赡养爷爷的责任名单里,但我觉得自己有义务给耄耋之年的爷爷一份温暖,于是,我决定要接爷爷来我家住些时日。
那是一个阳光温暖的上午,我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给爷爷专门收拾出一间干净又整洁的卧房来,在他的床头还特意装了一盏起夜的台灯,又摆上几盆像样的花草。我想,爷爷需要的不仅仅是吃饱饭,他和我们一样,同样也需要一份惬意又舒适的生活环境。
“姑姑,让爷爷去我家住几天吧?”做好迎接爷爷的所有准备,我便驾车来到姑姑家中。姑姑是爷爷唯一的女儿,但家里条件不好,姑父常年患疾,家里房子又遇上拆迁,只能临时租住在邻居家的一间老屋子里,空间极其狭小,爷爷住在那里,显得多余又拥挤。
“不去,去你家干啥?就让他在这儿呀!”姑姑看着墙角晒太阳的爷爷,有点无奈地说。爷爷耳背,听不清我们说啥,谁说话他就看谁的脸。
“爷爷,走,去我家住几天哩!”我弯下腰大声对爷爷说。爷爷怔了一下,笑了,咧着只剩一颗牙齿的嘴巴,说:“叫我去你家住哩?”说着就看姑姑的脸,姑姑笑了,我也笑了,这样我就把爷爷带回了我家。
爷爷来了,家里仿佛突然间充实了很多。我家的新房子新院子,还有爷爷的新房间,都让他有一种新鲜感,不停地在我的屋里院中走来走去,东瞧瞧,西看看,就像一个好奇的孩童。爷爷大概也没有想到,那个他曾经并没有多么关注的小孙女,今天还会对他尽一份孝心吧?嘿嘿!为了证明我可以让爷爷在这里过得很舒心,我把他的早中晚餐,还有日用起居,都一一作了规划安排,大致如此:
早餐,红枣小米粥,一到两个小菜,外加一个煎蛋;午饭,常是爷爷喜欢的大米,菜要两肉一素须有一汤。爷爷爱吃甜食,舀饭之前,我就把冰箱里备好的煮饼拿出来切片,用蒸锅蒸软后,再用筷子一片压着一片码放在他碗中。爷爷每端起碗,便要乐得看半天;晚饭,大多是汤面,或者疙瘩汤,但一定要有煎饼或者油泡、饼子之类配餐。爷爷胃口好,从来不对饭菜挑咸拣淡,每顿吃得都很香。我喜欢看爷爷吃饭,也喜欢变着花样地给爷爷做饭,被人需要,真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情。爷爷吃完了饭,搁下碗,坐上一会儿,见我开始洗碗,自己便慢悠悠的地起身往外散步去。
爷爷喜欢每天走路,认识爷爷的人都知道爷爷这个特点,许多不认识爷爷的人,也会因为这个成日在马路上惬意行走的老人,而频频回头。不管什么季节,在谁家寄住,方圆数十里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爷爷熟悉的身影。时常,他一个人默默地站着,静静地看着远方;也时常一个人,一晌一晌地坐在路边石阶上,呆呆地看着来往行人,若能碰巧遇到个故人或者晚辈,再能亲热地跟他聊上几句,那便是他一天中最有意义的事情。那会儿,经常有人夸爷爷身体好,我便自豪地说,走路就是他长寿的秘方。我常想,如果脚印可以在路上留存,大概多半个县城都是爷爷的印记罢。爷爷没戴过手表,没用过手机,但他总能准确地掌握回家吃饭的时间,时常,饭舀进碗里还不见人,刚要出去寻找,他就笑眯眯地进了门。手里提着那个我给他外出专用的茶杯,像个孩子一样举着,告诉我说:“看,水喝完啦!糖分了路上的一个老汉,也吃完啦!”因为耳朵背,我和他说话总要好几遍地吆喝,尽管他用手圈着耳朵想要努力听明白,但最终还是一脸懵懂,我就不说了,对他笑,他自己也笑。
爷爷住在院里的另外一间屋子,因为房子大房间多,那个地方不曾有人住过。爷爷来了,那个屋里的灯亮了,柔柔的灯光透过咖色的纱窗,成全了夜里小院完整的风景。也许是我过于喜爱那夜空下的安宁,也许是我太惦念屋里那个看我长大的老人,每晚睡前,我总是忍不住要到爷爷窗下待一会儿。爷爷大概没睡,我听到屋里略有翻书的声音。爷爷喜欢看书,尤其喜欢看有我的文章的书。夜深了,我久久依恋着,不愿睡去,守着那扇亮着的窗,任由一阵阵温馨在心头翻涌,我对自己说,这大概是我最好的幸福罢。
“爷爷,他们不接你,你就在这住着,我养你!”我拉着爷爷的手对他嚷。爷爷笑一下,就沉默了,再不说话,我便想哭。
差不多快到第四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午饭后,爷爷出去走路,至黑都没回来。那么大年纪了,好害怕路上出点意外。一颗心跳到嗓子眼,我一边给姑姑他们打电话,一边往爷爷常去的地方跑。最后,婶婶打来电话说,爷爷刚进她家门。爷爷就这样走了,没有人来接他,他自己走了,到他认为该轮到的儿子家去了。
我心里突然间空落落地,像面对空荡荡的屋子,无所适从。
爷爷走后,我的生活又回到原来的样子,餐饭变得快捷简单,甚至生活也开始懒散,但也轻松了许多。
有一天,我正要出门办事,爷爷突然来了,见了我,笑得跟花儿一样,一直对我笑着。我从没见过爷爷那么开心。我问他怎么突然来了呀,他说来拿几件换洗衣服。爷爷上次走的时候,并不曾带走任何行李。我赶紧让他进屋坐下,顺手就燃了煤气,添了水,煨下五个荷包蛋。不知为什么,我像有强迫症一样,总怕爷爷吃不饱,吃不好,每次见面,不管在哪儿,总是会想办法塞给他一些吃食。爷爷还是坐在他常坐的那把椅子上,笑眯眯的看着我为他忙活。当我把又白又圆的荷包蛋端到爷爷跟前时,他的嘴巴翕动了两下,又看着我帮他把糖加好,搅了搅,便一口一口地吃喝起来。爷爷吃得那么香,那么忘乎所以,我看着他,一种久违的幸福感,在心里荡漾。
爷爷走了,我们的世界安静了,晚辈的生活也安然了。少了一种责任和义务,也埋葬了那种膝下承欢的天伦之乐;爷爷走了,在我心中留下了永远的愧疚,我时常想,爷爷那次回来,如果我能把他好好留住,好好侍奉,不知道他会不会这么快离开……爷爷走了,他把最灿烂的笑容留在了我的心中,把最依恋的眼神留在了我的院里。他那最后一笑啊,是想留下来示好,还是对晚辈的某种感激……也许,他只是一种疼爱,一种对晚辈无尽地疼爱。可,不管是什么,无论再愧疚,爷爷是永远地去了,那至亲至爱的亲情,永远逝去了。
朱自清亲情的散文篇五
小时候,常常听爸爸谈起大姑家的表哥,谈起他们小时候的艰苦岁月。那时候新中国还没有成立,那种困苦的环境现在只能在书本里能看到。爸爸说,表哥只比他小几岁,不知是在那一年大姑去世了,无依无靠的表哥只好生活在姥姥家里,也许是年龄相差无几的原因吧,爸爸和表哥从表面上已看不出是舅舅和外甥的关系,他们依然成了好朋友,一起吃住,一块赤着脚在原野中尽情地玩耍。
表哥天资聪颖,那时候上学对穷人家的孩子来说还是一种奢望。为了让表哥能去上学,全家人可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把表哥送去了集贤镇(旧社会叫集贤县)一所私塾。就这样表哥一年年地在姥姥和舅舅的呵护中渐渐长大。那时候好像还没有什么高考制度,但读书人依然被穷人看做弥足地珍贵。由于表哥书读的多,在以后的生活里,他并没有留在农村。新中国成立后,表哥有了工作,也不知是哪一年,被分配到了双鸭山市宝山广播站,直到退休。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随着岁月的流逝,爸爸还是经常谈起表哥,常念叨,广云忘本哩,这些年也不回舅舅家看一看.....我也常常望着爸爸的脸庞,好像在寻找表哥当年的模样,但从爸爸渐已苍老的面容中已联想不出表哥的摸样,直到2000年爸爸去世,就再也没有表哥的消息了。
2011年12月4日,哥哥意外地在井下遭遇重伤,为了更好地给予治疗,家里人决定还是去哈市治疗为妥,可想到在遥远的大都市举目无亲,假如没有床位该怎么呢!在这关键时刻,远在山东的老姑来电话说,广云现在在哈尔滨住,去找他吧,他会帮你的。为了慎重起见,家里人决定先让我拿ct片子去看看再说。
汽车疾驶在哈同高速公路上。至改革开放以来,公路两旁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面貌日新月异,那笔直的公路,那林立的的楼房,还有呼啸而过的高山和大树,此时我已无暇欣赏两旁的美丽景色,满脑子只是想着,从小到大从未见过表哥,那岁月飘去的亲情现在还能寻到吗?听说表哥家里的孩子工作和地位都比较显赫,家里的条件自不必说,光小汽车就有五台,在这以金钱为主体的社会里,表哥一家还能‘认识’我吗!我一路思考遐想着,直到终点安发桥还没有打消这一顾虑。下了车,站在人山人海的大街上,我早已辨不清了东南西北,由于事先有老姑的电话约定,我远远地眺望安发桥的尽头,一位老人蓦然地映入我的眼帘,穿着深蓝色的半截外衣,带着一顶时髦的前进帽,由于天气寒冷,从他的呼吸中已然飘出了淡淡的白云,清瘦的脸庞在云雾中时隐时现,可从老姑的表述中我还是认出了他就是表哥。我匆忙地迎了过去,一时间把早已想好的问候卡在喉咙里。看到我尴尬的表情,表哥好似早已认识了我,定定地看着,拉着我的手说,像我五舅的摸样(爸爸排行老五).就这一句话,在我回来的许多日子里,我常常地想着,它如一抹浓墨重彩的山水画,描述着表哥一家并没有忘记远在农村的亲人,那血溶于水的亲情,其实一直在表哥的生活中演绎着。表哥指着不远处停靠的小轿车说,玉伟(表哥二儿子)在哈市华能集团工作,现在正和荷兰的客商谈判,但他还是抽出一点时间来接你们.............听到表哥的话,我一时竟不好意思起来,在以商业为中心的理念中,耽误人家的时间在我的心理平添了一股淡淡的歉意。对于我的歉意,表哥仍坚持以长辈的口吻说,孩子们的事咱就别去管他。其实我的年龄和小侄都是1966年生人,在同龄人的对视中,我怎么也表现不出一个长辈的气派来,可小侄一口一个小叔地叫着,拉着我们去哈市最好的医院二院把正在手术中的教授叫出来,等看完片子把我们又拉回表哥家中,此时已是万家灯火夜色阑珊的时候了,已是72高龄的表哥仍顾不上休息,到楼下点菜去了。
在表哥家宽敞漂亮的客厅里,我的眼睛四处逡巡着,那些漂亮的家具,那些时髦的家用电器,我却怎么也找不出表哥童年的影子来。一件件小古董,一摞摞书籍,我猜想已是古稀之年的表哥并不孤独,他有孝顺的孩子,有生活中的乐趣和爱好,在以小康为标准的家庭中,表哥的生活应该是很幸福的。表哥的知识非常丰富,他和我谈起社会与家庭,个人与群体,也谈政治军事,谈祖国的发展现状,对于我的审视观点表哥还是大多赞同的。表哥说,一个人要多学知识,没有知识的人是没有价值的。他还说,你知道几十年来我为什么没有去舅舅家呢!那是困苦而所迫呀。姑父多年瘫痪在床,自己家里孩子又多,这么一副重担,几十年来一直是表哥在扛着。表哥深知知识的重要性,两儿两女都是大学生,也都有了很好的工作,其实孩子们的锦绣前程不正是表哥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出来的吗!此刻我的心中猛然生出对表哥的无比敬意。我想象着在那困苦的岁月中,表哥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上班下班,如一头任劳任怨的孺子牛,辛勤地耕耘着那一份希望的田地,没有任何怨言,其实在他的心底里一直是在用热血播种着未来,那就是用知识把孩子武装成人,完成一个做父亲的应尽责任。
那一夜我们谈了很多很多。表哥常常把话题转到爸爸的身上,说他小时候五舅对他特别好,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在姥姥家的成长历程。他指了指厚厚一摞《朱镕基秒语录》和《走进钱学森》说,你喜欢读书,这些就送给你吧,从中你会领悟到一个做人的准则。我非常珍惜表哥这一珍贵的馈赠,他比任何一种以金钱为礼物的馈赠都要宝贵,那就是对亲人的真诚。
汽车疾驶在回来的路上,我手捧着一摞摞书籍,想着和表哥临别时的约定,表哥说他要整理复印一些相片给我寄来,让远在农村的弟弟妹妹看看。想到他的叮咛嘱托,我的眼中渐渐涌出晶莹的泪花,那将寄来的照片,不正是表哥一双热情的双手,把漂流已久的亲情一串串地而串起来嘛!
朱自清亲情的散文篇六
二毛的娘死了。二毛的娘是带着对大毛的遗憾走的,老太太临死前还在喊着大毛的名字。二毛跪在娘的身边拉着娘的手,哭着告诉娘,没能把大毛喊来。
院子里,当家子、亲戚好友、乡里乡亲们说叨着不懂事理的大毛,娘再不对,都是娘。
1、翠花嫂嫁到俺们村40多年了。
那年,大毛10岁,二毛8岁,翠花嫂的丈夫死了。有人劝翠花嫂改嫁,可她为了俩孩子,一直没有再找人家。
那个年代,家家都混得都很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更何况,一个女人家带着两个孩子,没有男人的家,就像缺少了顶梁柱。就是这样,翠花嫂还是咬咬牙,一天一天的熬了过来。
大毛和二毛上学的时候,是村里有名的好孩子。和他俩一块上学的还有大丑和丫丫。
家里穷,供养不起两个孩子都上学。
没办法,翠花嫂让大毛小学毕业后,就回家跟着自个做家务活。二毛也是个争气的孩子,在校的时候,知道娘和哥哥不容易,学习一直名列前茅。
看着懂事好学的二毛,翠花嫂和大毛商量:“娘知道对不起你。咱一起供二毛把学读下来吧。”大毛心里总觉得不舒服,还是顺从娘点了头。
二毛真是个好孩子,那年他和丫丫一块儿考入了隆尧师范。
后来,大毛娶了媳妇,有了孩子。
那时,刚刚分了地,家里的日子才刚刚有好转。翠花嫂把仅有的三间北屋翻盖了,给大毛当了新房。自己搬进了西屋。二毛回来的时候就和自己一起住在西屋。
二毛和丫丫分到在本村小学教书。
大毛结婚后,过了一段时间。
有一天,大毛对翠花嫂说:“娘,你看。种地没有牲口不能干活。我买了一头毛驴,我得在西屋里喂驴,你去学校和二毛住吧。”在一旁的儿媳妇,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自己的婆婆。
二毛找大毛说:“哥,我刚毕业。先让娘在家住,等我有了家,我来养咱娘行不”。大毛没有丝毫退让。对二毛说:“当初,家里条件是不好,可娘偏心。让你上了师范,可就让我回家种地。你看大丑,丫丫。上学时不如我,现在在镇上也成了干部,丫丫也和你一样成了老师。要当初,娘让我上学,没准我早当上县委书记了。没准丫丫早成了俺媳妇了。”
翠花嫂在一边不住的流泪:“是啊,当初都怨那死鬼死的早,狠心的丢下我们不管了,要不怎么能让大毛种地呢。”
屋外下起了雨,二毛用自行车,驮着娘的铺盖卷来到了学校。
大毛发誓从此以后与娘不相往来。
2、二毛在村东盖起了房子,娶了媳妇。媳妇是丫丫。原来,丫丫一直喜欢着二毛。大毛从心里恨二毛,啥好事都让二毛赶上了。更恨丫丫嫁给了二毛。二毛、丫丫不和大毛计较,兄弟毕竟是兄弟,砸断骨头还连着筋哩。翠花嫂和二毛一起住。丫丫知道婆婆不容易,对翠花嫂就像亲娘。翠花嫂时常带着点东西到大毛的家看看。大毛不让翠花嫂进门,翠花嫂可总觉得儿子毕竟是自己的儿子。
二毛因工作能力好,教学突出,被教委任命为校长,大毛到学校找到二毛。让二毛找镇里让他在村里当个村长。二毛觉得毕竟是自己亲哥,就应允了。大毛成了村长。
成了村长的大毛,成了官。可是,邻家大丑在镇上已当了副乡长,时常开着奥迪三圈回家。呵,别提多神气。大毛打心里更是嫉恨娘和二毛,要是娘当初让我上学,我早当上县委书记了。
大毛见到娘和二毛就来气,有人想劝说劝说大毛,大毛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大毛的媳妇对婆婆也是不正眼待。后来,谁和他提他娘,他就和谁急。
就是这样,过年过节,二毛还是和娘商量着总是给大毛送去点肉啥的。大毛来者不拒。
大毛有儿子了。翠花嫂高兴地买了东西去看孙子,东西大毛两口子留下了,娘却被撵了出来。
老少爷们说大毛:“你大小也是个官。过年过节,你不给你娘了,反过来让你娘和兄弟给你肉。你丢人不”。
大毛振振有词的说:“那是他们娘俩欠俺的”。
3、又过了几年,二毛成了教育局局长了。大毛更是觉得不公平了。
大毛的儿子上学不好好读书,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二毛给他找个工作不好好干,二十五六了还娶不上媳妇。给大毛的儿子一提亲,对方一打听,自己的娘都不管,这家能好了。再加上孩子不争气。村里人们说,那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大毛看着二毛的日子越过越好,心里越来气:“如果当初不是你,我怎能这样。我的`儿子怎能说不上媳妇。”
二毛面对不懂礼节的大毛,生不得气着不得急,怎么也是一奶同胞兄弟。
翠花嫂年近七十了。
好在二毛两口子孝顺,也算是享了福了。一天,翠花嫂总觉得胃里不舒服。二毛赶紧带娘去医院,一查胃癌晚期。
翠花嫂要二毛去叫大毛来。
二毛告诉大毛,娘得了胃癌,要见他。大毛考虑了一会儿,就和二毛来到了二毛家。走到家门口,丫丫走了出来,一看大毛来了,赶紧往家里请。大毛一看二毛的房子比自己的房子宽敞明亮,心里就又来气了。扭头就走了。
大毛对二毛和丫丫说:“你们若要我去认娘。也行,你得答应给我儿子盖房娶媳妇。”
不管二毛和丫丫咋喊,就是不回头。
二毛两口子气的直跺脚。
4、翠花嫂死了。
乡里乡亲们实在看不下去了,要求老支书把大毛从村委班子里撤下来。大毛吓坏了,找到了老支书。老支书对大毛说:“你娘不是二毛自己的吧。要不是二毛给你找,你凭啥当村长。你娘死了,你还发混呀。
你还要二毛操办你儿子的婚事。你丢人不,你给乡里乡亲起个啥带头。从明天你就别在村里干了。”
大毛一听,不让他在村里干了。就急了,他对老支书说:“叔,你说咋办我就咋办。我这次听您的。可不能让我不当村长,要不我儿子更娶不上媳妇了。”
老支书先让他操办完他娘的丧事再说。
村里老少爷们的话让大毛抬不起头。他厚着脸皮走进了二毛家。翠花嫂的二弟看到大毛来了,抄起棒子要打大毛。二毛跪在舅舅面前拉着不让打。
大毛要当孝子,可是舅舅不干。对二毛两口子说:“咱说好了,大毛不能哭你娘。当初,我说他多少次他不听,还和你娘断了道。今天这事,说啥也不能听你两口子的。他和你娘不相往来,这会儿他要当孝子办不到。”
最后,在大家的劝说下,舅舅说大毛:“你哭你娘也行。你拿出3万块钱来。”大毛哭丧着脸说:“舅舅,俺家里总共才8000块钱。俺没钱。”
“那你滚蛋,”舅舅发了话。
大毛借了一圈,凑了块钱。
舅舅怕大毛不认账,当着老支书的面让大毛打了一欠条。老支书说:“这钱我先给你垫上,以后你有了钱再给我。”
大毛一应百应。
二毛的儿子觉得大伯也是忒不像话,在一旁对舅姥爷说:“那大伯站在哪呀。站我后面不合适呀。”
二毛训斥儿子:“听你舅姥爷的,你少插话。”
二毛的儿子看看二毛不哈声了。
最后,还是应了舅舅的话,让二毛当大孝子,大毛站在二毛后面。
出殡那天,人们在一旁议论着看着大毛的笑话。
5、安葬完翠花嫂。二毛让老支书把大毛叫到了家里,当着舅舅的面,把一万块钱给了大毛,把欠条撕了。
舅舅说:“二毛,你钱多,给我。”二毛也知道,那是舅舅生大毛的气。二毛给大毛使眼色,大毛赶紧跪倒了舅舅的面前。对舅舅说以后和二毛不再闹矛盾了。
因为当爹的没有起好带头,到头来自己儿子也娶不上媳妇。从那以后,大毛成了村里人教育孩子的议论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