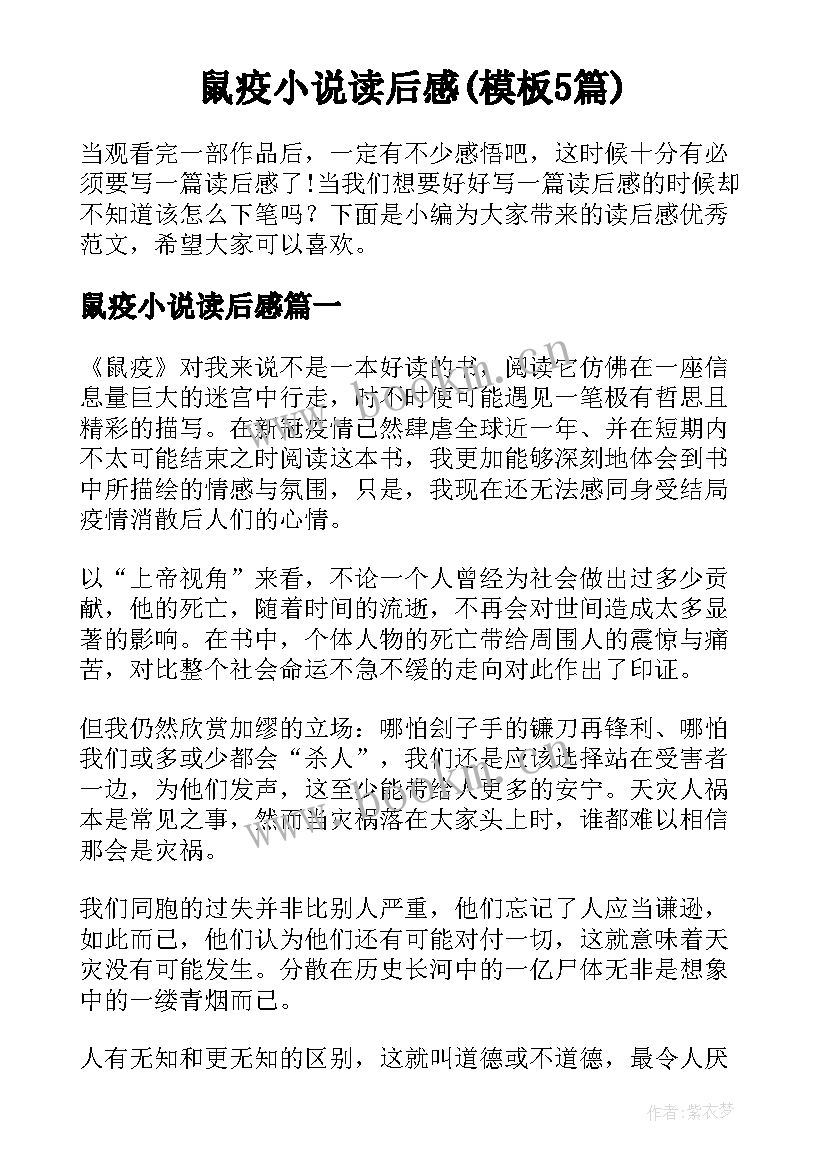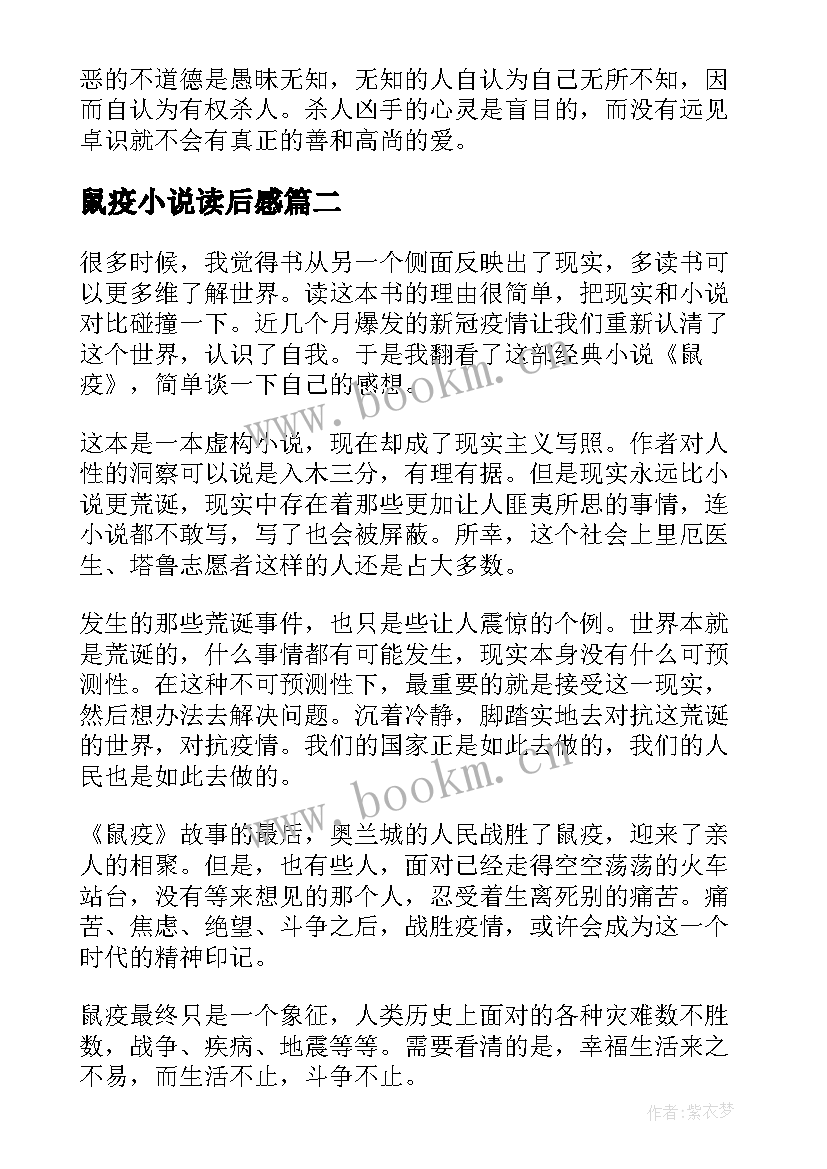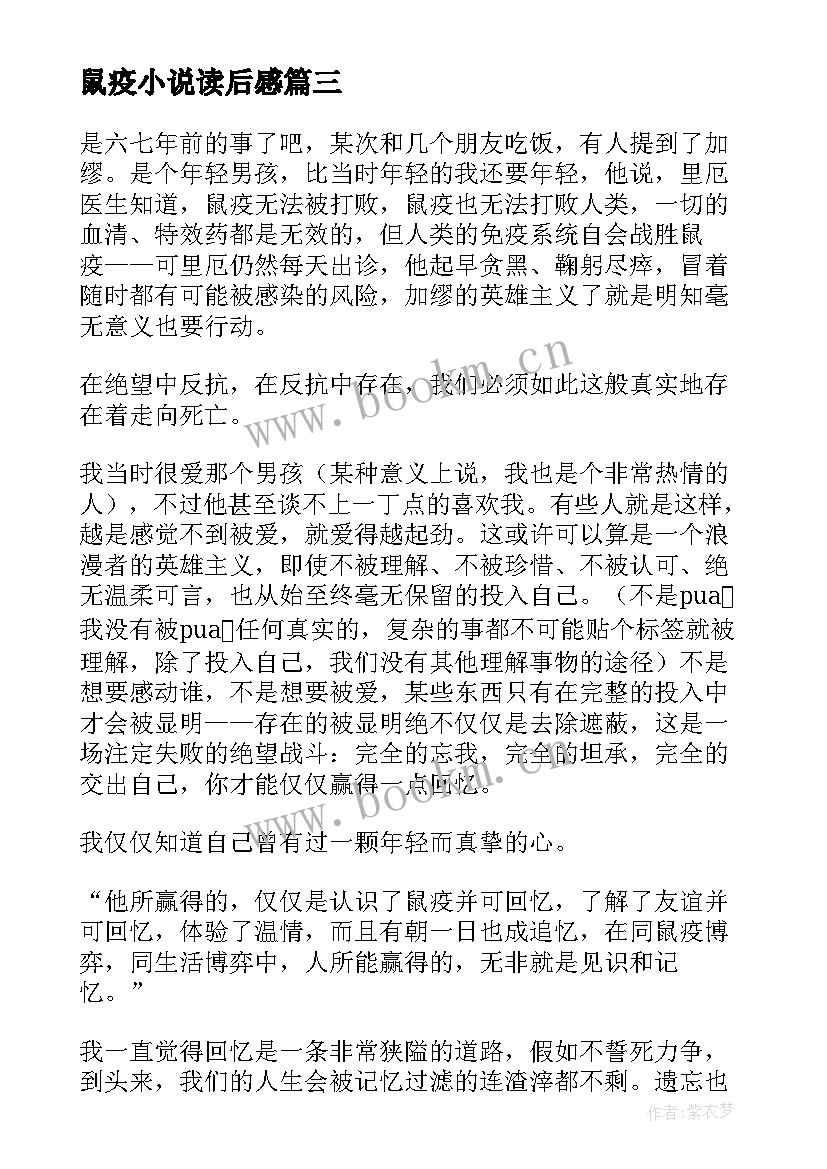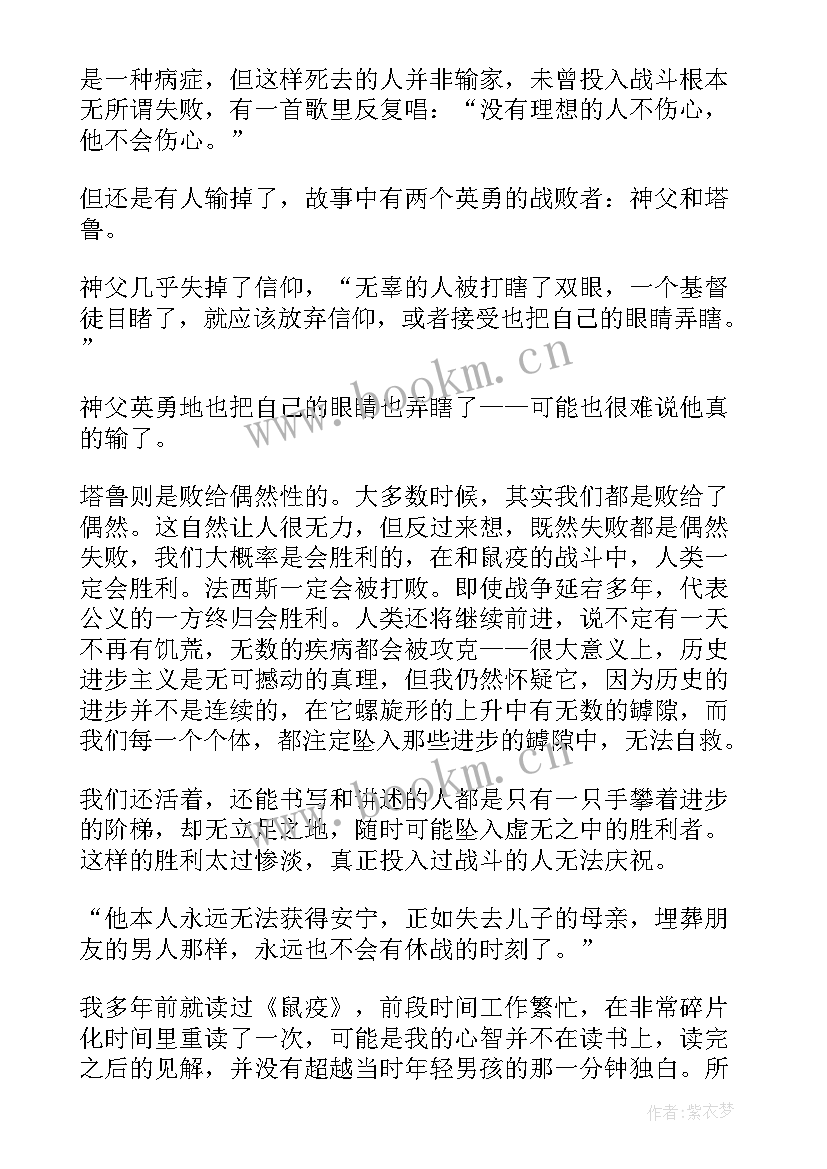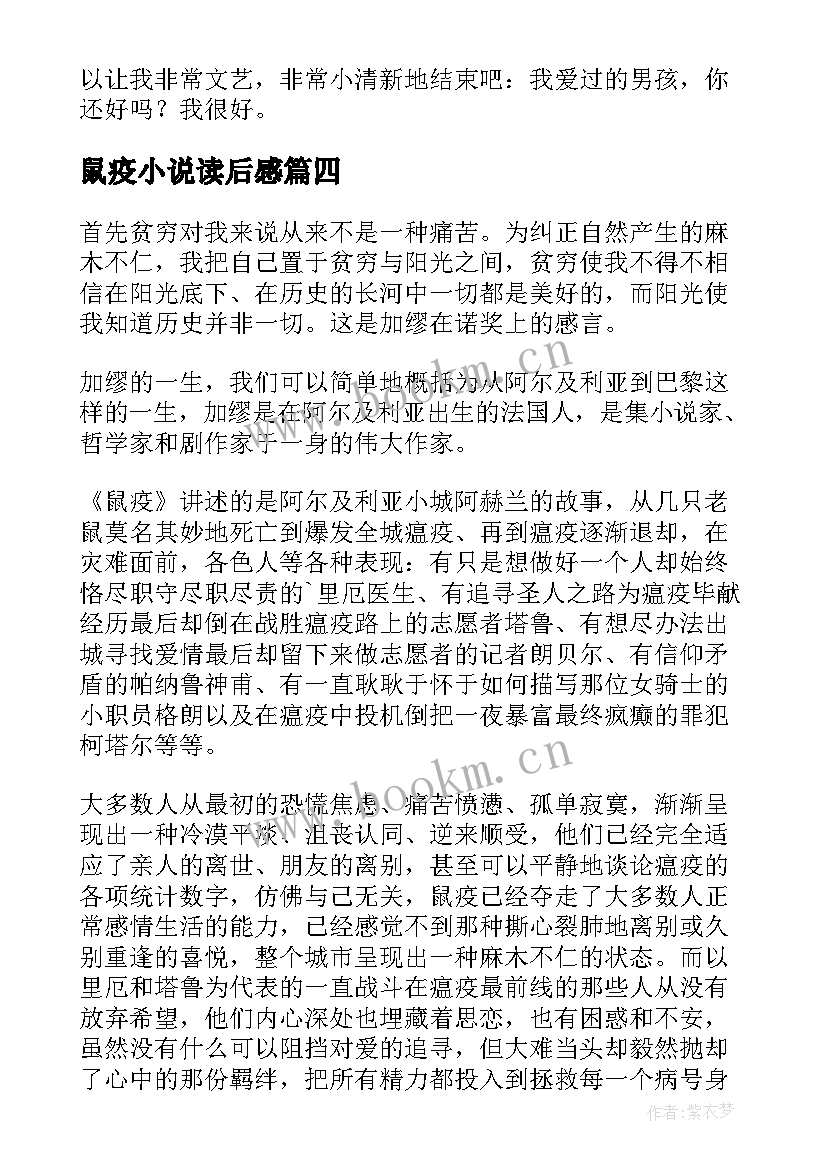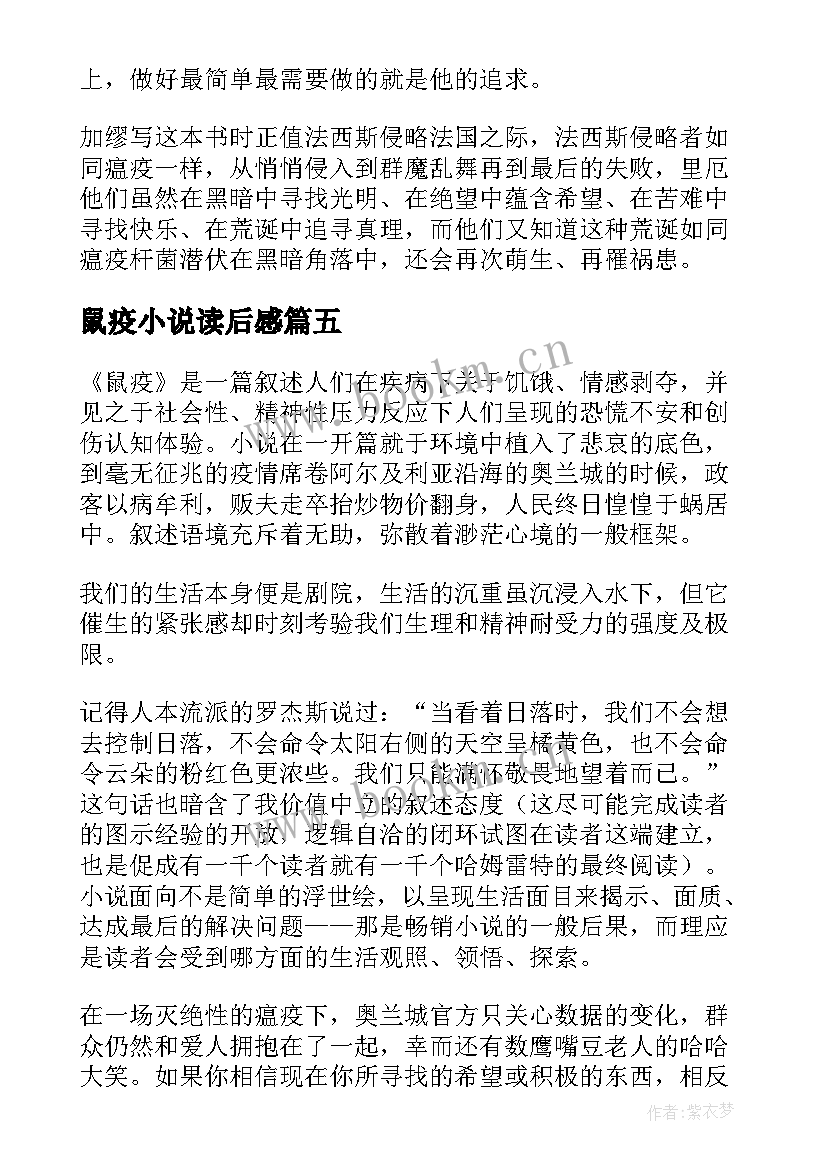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鼠疫小说读后感篇一
《鼠疫》对我来说不是一本好读的书,阅读它仿佛在一座信息量巨大的迷宫中行走,时不时便可能遇见一笔极有哲思且精彩的描写。在新冠疫情已然肆虐全球近一年、并在短期内不太可能结束之时阅读这本书,我更加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书中所描绘的情感与氛围,只是,我现在还无法感同身受结局疫情消散后人们的心情。
以“上帝视角”来看,不论一个人曾经为社会做出过多少贡献,他的死亡,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再会对世间造成太多显著的影响。在书中,个体人物的死亡带给周围人的震惊与痛苦,对比整个社会命运不急不缓的走向对此作出了印证。
但我仍然欣赏加缪的立场:哪怕刽子手的镰刀再锋利、哪怕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杀人”,我们还是应该选择站在受害者一边,为他们发声,这至少能带给人更多的安宁。天灾人祸本是常见之事,然而当灾祸落在大家头上时,谁都难以相信那会是灾祸。
我们同胞的过失并非比别人严重,他们忘记了人应当谦逊,如此而已,他们认为他们还有可能对付一切,这就意味着天灾没有可能发生。分散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亿尸体无非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而已。
人有无知和更无知的区别,这就叫道德或不道德,最令人厌恶的不道德是愚昧无知,无知的人自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因而自认为有权杀人。杀人凶手的心灵是盲目的,而没有远见卓识就不会有真正的善和高尚的爱。
鼠疫小说读后感篇二
很多时候,我觉得书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现实,多读书可以更多维了解世界。读这本书的理由很简单,把现实和小说对比碰撞一下。近几个月爆发的新冠疫情让我们重新认清了这个世界,认识了自我。于是我翻看了这部经典小说《鼠疫》,简单谈一下自己的感想。
这本是一本虚构小说,现在却成了现实主义写照。作者对人性的洞察可以说是入木三分,有理有据。但是现实永远比小说更荒诞,现实中存在着那些更加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连小说都不敢写,写了也会被屏蔽。所幸,这个社会上里厄医生、塔鲁志愿者这样的人还是占大多数。
发生的那些荒诞事件,也只是些让人震惊的个例。世界本就是荒诞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现实本身没有什么可预测性。在这种不可预测性下,最重要的就是接受这一现实,然后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沉着冷静,脚踏实地去对抗这荒诞的世界,对抗疫情。我们的国家正是如此去做的,我们的人民也是如此去做的。
《鼠疫》故事的最后,奥兰城的人民战胜了鼠疫,迎来了亲人的相聚。但是,也有些人,面对已经走得空空荡荡的火车站台,没有等来想见的那个人,忍受着生离死别的痛苦。痛苦、焦虑、绝望、斗争之后,战胜疫情,或许会成为这一个时代的精神印记。
鼠疫最终只是一个象征,人类历史上面对的各种灾难数不胜数,战争、疾病、地震等等。需要看清的是,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而生活不止,斗争不止。
鼠疫小说读后感篇三
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吧,某次和几个朋友吃饭,有人提到了加缪。是个年轻男孩,比当时年轻的我还要年轻,他说,里厄医生知道,鼠疫无法被打败,鼠疫也无法打败人类,一切的血清、特效药都是无效的,但人类的免疫系统自会战胜鼠疫——可里厄仍然每天出诊,他起早贪黑、鞠躬尽瘁,冒着随时都有可能被感染的风险,加缪的英雄主义了就是明知毫无意义也要行动。
在绝望中反抗,在反抗中存在,我们必须如此这般真实地存在着走向死亡。
我当时很爱那个男孩(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个非常热情的人),不过他甚至谈不上一丁点的喜欢我。有些人就是这样,越是感觉不到被爱,就爱得越起劲。这或许可以算是一个浪漫者的英雄主义,即使不被理解、不被珍惜、不被认可、绝无温柔可言,也从始至终毫无保留的投入自己。(不是pua,我没有被pua,任何真实的,复杂的事都不可能贴个标签就被理解,除了投入自己,我们没有其他理解事物的途径)不是想要感动谁,不是想要被爱,某些东西只有在完整的投入中才会被显明——存在的被显明绝不仅仅是去除遮蔽,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绝望战斗:完全的忘我,完全的坦承,完全的交出自己,你才能仅仅赢得一点回忆。
我仅仅知道自己曾有过一颗年轻而真挚的心。
“他所赢得的,仅仅是认识了鼠疫并可回忆,了解了友谊并可回忆,体验了温情,而且有朝一日也成追忆,在同鼠疫博弈,同生活博弈中,人所能赢得的,无非就是见识和记忆。”
我一直觉得回忆是一条非常狭隘的道路,假如不誓死力争,到头来,我们的人生会被记忆过滤的连渣滓都不剩。遗忘也是一种病症,但这样死去的人并非输家,未曾投入战斗根本无所谓失败,有一首歌里反复唱:“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他不会伤心。”
但还是有人输掉了,故事中有两个英勇的战败者:神父和塔鲁。
神父几乎失掉了信仰,“无辜的人被打瞎了双眼,一个基督徒目睹了,就应该放弃信仰,或者接受也把自己的眼睛弄瞎。”
神父英勇地也把自己的眼睛也弄瞎了——可能也很难说他真的输了。
塔鲁则是败给偶然性的。大多数时候,其实我们都是败给了偶然。这自然让人很无力,但反过来想,既然失败都是偶然失败,我们大概率是会胜利的,在和鼠疫的战斗中,人类一定会胜利。法西斯一定会被打败。即使战争延宕多年,代表公义的一方终归会胜利。人类还将继续前进,说不定有一天不再有饥荒,无数的疾病都会被攻克——很大意义上,历史进步主义是无可撼动的真理,但我仍然怀疑它,因为历史的进步并不是连续的,在它螺旋形的上升中有无数的罅隙,而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注定坠入那些进步的罅隙中,无法自救。
我们还活着,还能书写和讲述的人都是只有一只手攀着进步的阶梯,却无立足之地,随时可能坠入虚无之中的胜利者。这样的胜利太过惨淡,真正投入过战斗的人无法庆祝。
“他本人永远无法获得安宁,正如失去儿子的母亲,埋葬朋友的男人那样,永远也不会有休战的时刻了。”
我多年前就读过《鼠疫》,前段时间工作繁忙,在非常碎片化时间里重读了一次,可能是我的心智并不在读书上,读完之后的见解,并没有超越当时年轻男孩的那一分钟独白。所以让我非常文艺,非常小清新地结束吧:我爱过的男孩,你还好吗?我很好。
鼠疫小说读后感篇四
首先贫穷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种痛苦。为纠正自然产生的麻木不仁,我把自己置于贫穷与阳光之间,贫穷使我不得不相信在阳光底下、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切都是美好的,而阳光使我知道历史并非一切。这是加缪在诺奖上的感言。
加缪的一生,我们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从阿尔及利亚到巴黎这样的一生,加缪是在阿尔及利亚出生的法国人,是集小说家、哲学家和剧作家于一身的伟大作家。
《鼠疫》讲述的是阿尔及利亚小城阿赫兰的故事,从几只老鼠莫名其妙地死亡到爆发全城瘟疫、再到瘟疫逐渐退却,在灾难面前,各色人等各种表现:有只是想做好一个人却始终恪尽职守尽职尽责的`里厄医生、有追寻圣人之路为瘟疫毕献经历最后却倒在战胜瘟疫路上的志愿者塔鲁、有想尽办法出城寻找爱情最后却留下来做志愿者的记者朗贝尔、有信仰矛盾的帕纳鲁神甫、有一直耿耿于怀于如何描写那位女骑士的小职员格朗以及在瘟疫中投机倒把一夜暴富最终疯癫的罪犯柯塔尔等等。
大多数人从最初的恐慌焦虑、痛苦愤懑、孤单寂寞,渐渐呈现出一种冷漠平淡、沮丧认同、逆来顺受,他们已经完全适应了亲人的离世、朋友的离别,甚至可以平静地谈论瘟疫的各项统计数字,仿佛与己无关,鼠疫已经夺走了大多数人正常感情生活的能力,已经感觉不到那种撕心裂肺地离别或久别重逢的喜悦,整个城市呈现出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而以里厄和塔鲁为代表的一直战斗在瘟疫最前线的那些人从没有放弃希望,他们内心深处也埋藏着思恋,也有困惑和不安,虽然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对爱的追寻,但大难当头却毅然抛却了心中的那份羁绊,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拯救每一个病号身上,做好最简单最需要做的就是他的追求。
加缪写这本书时正值法西斯侵略法国之际,法西斯侵略者如同瘟疫一样,从悄悄侵入到群魔乱舞再到最后的失败,里厄他们虽然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绝望中蕴含希望、在苦难中寻找快乐、在荒诞中追寻真理,而他们又知道这种荒诞如同瘟疫杆菌潜伏在黑暗角落中,还会再次萌生、再罹祸患。
鼠疫小说读后感篇五
《鼠疫》是一篇叙述人们在疾病下关于饥饿、情感剥夺,并见之于社会性、精神性压力反应下人们呈现的恐慌不安和创伤认知体验。小说在一开篇就于环境中植入了悲哀的底色,到毫无征兆的疫情席卷阿尔及利亚沿海的奥兰城的时候,政客以病牟利,贩夫走卒抬炒物价翻身,人民终日惶惶于蜗居中。叙述语境充斥着无助,弥散着渺茫心境的一般框架。
我们的生活本身便是剧院,生活的沉重虽沉浸入水下,但它催生的紧张感却时刻考验我们生理和精神耐受力的强度及极限。
记得人本流派的罗杰斯说过:“当看着日落时,我们不会想去控制日落,不会命令太阳右侧的天空呈橘黄色,也不会命令云朵的粉红色更浓些。我们只能满怀敬畏地望着而已。”这句话也暗含了我价值中立的叙述态度(这尽可能完成读者的图示经验的开放,逻辑自洽的闭环试图在读者这端建立,也是促成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最终阅读)。小说面向不是简单的浮世绘,以呈现生活面目来揭示、面质、达成最后的解决问题——那是畅销小说的一般后果,而理应是读者会受到哪方面的生活观照、领悟、探索。
在一场灭绝性的瘟疫下,奥兰城官方只关心数据的变化,群众仍然和爱人拥抱在了一起,幸而还有数鹰嘴豆老人的哈哈大笑。如果你相信现在你所寻找的希望或积极的东西,相反在未来有可能都不存在,那么我们在两极的体验终究回归于中庸,回归于日常生活的现象场。这即是永恒的图示。而这个感悟,应出自里厄:“我不知道它(同鼠疫作斗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实事求是)的普遍意义。但是就我而言,我知道它的意思是做好我的本分工作。”
关于《鼠疫》小说议题的采择:加缪在对灾难的习惯比灾难本身更可怕的问题空间下推演出人类对恐惧的偏离本能,精确投射出基于灾难下社会常模中的一组习得性无助。而基于此而开展的系列人性的历史性的再现,加缪向我们回答的却是文本之外——恐惧的强烈决定着人们的亲合倾向的程度,并引领人们走出晦暗而幽深的人性隧道。
我们就不需要这类的角色期待,更不需要这一类小说。我们总会这样去记忆的——情绪、情感体验具有两极对立性,人物角色的世界里有多少高贵的东西就有多少阴影的邪恶。这是加缪的哲学抱负,通过运用空间知觉及社会知觉,始终自觉地维持语言整体的绝对信念,全人类坚不可破的生存积淀——这些带有领悟色彩的认知修正了人们心中的固定倾向。
似乎按一切荒谬即真理这一魔咒,一切经典文本总离不开“人类永远无法彻底认知的荒谬”来临摹。《鼠疫》通过塑造的特型人物科塔尔——他认为疫情提供了以逃避正义惩罚并可实行他的阴暗市场行为的机遇。这令我发现了故事的普遍现象场——于道德故事中,维持适宜的价值中立,便能顺利把我们从已知经验中推向一个封闭的选项。然而加缪赋予《鼠疫》另外一个分量场,即往返穿梭荒诞的现实和理想两境。文本最终驱动出极致的人文意义——那就是第一句活着,第二句立即死去的意向行文。这是加缪在《鼠疫》中回答的道之所在。
《鼠疫》就像一个平行的剧本向我们呈现人性演化出现的退行性反复,令人诧异的是这些表现均呈现了稳定的一致性。在灾难症候适应群体中人们总会出现情绪倒错和淡漠,所以小说需要给文本赋予高级感,如此读者尚能以幸存者的觉悟——突困于文明和本能野蛮间的龃龉。
通过小说述谓现实境遇,我们在非典后,当下新冠疫情的漫长适应期,在时间前景的扩散下再现解决生活问题和社会联接问题上,解决他们取决你采用的是调幅还是调频倾向。